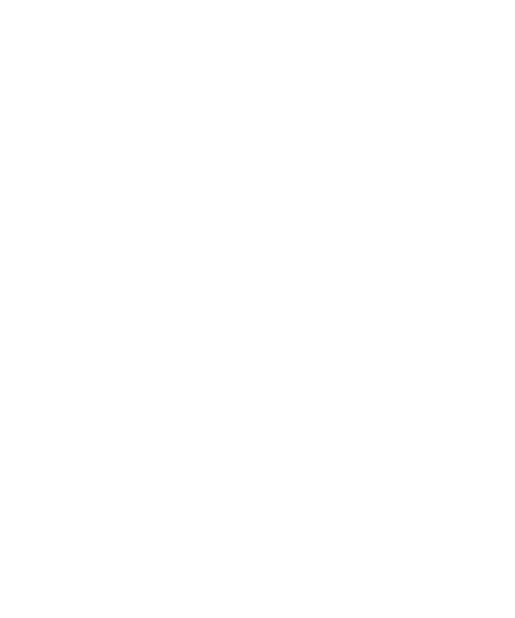柳振师
2001年10月,在朋友的帮助下,我来到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工作。半年之前的我,在阿克苏从事过装卸工、清洁工,兼职过保安。
有单位真好。每天清晨一睁眼,首先想到的是单位,每日里提及最多的字眼也是单位。当时,我的户口落在单位的门牌号上。同事开玩笑说,我是阿克苏最“富有”的人,仿佛整个文化艺术中心都是属于我的。
能够进入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工作,除了感谢朋友的推荐外,我还要感念在部队当过放映员的经历。由于我住的地方距离单位较远,每天需要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多公里路程,同事就利用午休时间帮我焊接一张床,搁在地下室的总机转换室里,还放置了一桌一椅。
我有些忐忑,担心不符合单位规定。同事安慰我,这是领导同意的,连桌椅都是领导准备的,知道我喜欢写作,特意搬来给我用。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切,刹那间,一股暖流遍布全身。
在单位工作的20年里,有6年多的时间我都是住在单位的。离开地下室,我的下一个住处是三楼放映室一个不规则的空间,那是通道的出口,在电梯的拐角,恰好可以搁置一张床。
我躺在三楼这张不大的床上开始做梦,关于生活的、爱情的、文学的梦。这一处面积不足18平方米的空间,却能让我思绪万千,有欢乐的、有悲伤的,欢乐和悲伤交织在一起,让我的思绪犹如脱缰的野马,一刻不能消停。又仿佛是谁在召唤着,让我不停地写呀写,将那些过往的事情、过往的情感记录下来,给自己一个交代。
我长期住在单位的事,惹得一些人不快。当新一任领导上任后,有人将这件事汇报上去。领导了解了始末后,在大会上这样说:“在这么一栋大楼里,有一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守着。有些人只看到这个人用了单位的水和电,却没有发现这个人对这栋楼的贡献,每天夜里,是这个人楼上楼下地跑着,关灯、检查水龙头……”他没有点名地向大家说了我所做的一切,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而我觉得肩上有了一份重担,每天下班及时关灯、关水龙头成了我的责任和义务。
新领导没有架子,他时常走进这处属于我的空间里。他第一次来的时候,拿起桌上一沓我写的长篇手稿翻看,看完几页抬头说:“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写短篇,写长篇,你还不具备驾驭的能力。”我点头应诺。此后,他每每在外就餐,总会给我打包一些吃食送来,如果我不在,他就把吃食挂在门把手上。
我停下长篇写作,开始写短篇,几篇散文陆续刊登在《阿克苏广播电视报》上。他读到后,把其中一篇散文《三张羊皮》的细节当着我的面或别人的面复述出来,尤其是文中的陈皮匠,他说,写得很有特点,让他一下就记住了这个人物。他的肯定成为我坚持写作的动力。在我的心里,他既是我的领导,又是我的兄长。
后来,单位人事再次变更,新上任的是一位女领导。数字电影的上马,加之人员编制的落实,人心定了,心就齐了,大家拧成一股绳,劲往一处使地开展各项工作,单位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。而我,由一名放映员被任命为电影经营科科长,有幸被派往上海参加全国影院经理培训班,使我深知营销策划在电影市场的竞争中是何等的重要。
我带领团队走出去搞“百家联盟”,让不同行业、不同场所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地开展资源共享,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、QQ群、网站等网络资源,彻底解决宣传经费欠缺的问题,使营销策划的宣传力度大大提升。四年来,我吃饭说的是电影,甚至晚上做梦也是与电影有关的事情。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上中层领导岗位,我感觉自己像一条纽带,既要照顾老同事、老班长的情绪,又要落实好领导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,得了焦虑症。我意识到是该放下的时候了,便辞去电影经营科科长的职务,做回一名普通的放映员。
即使我有了新的宽敞的居住之地,这处有限的空间依然是属于我的。我哭过、笑过、醉过、疯过,它一直默默地替我保守着秘密。只要踏进这处空间,我的心立马会静下来,看书、写字、练书法,散文集《我的阿克苏》就出自这处有限的空间里。
2016年3月,我去了一个叫木日开旦木村的村庄参加“访惠聚”驻村工作,我把在村里睡觉的床亲切地称为“革命的床”。这一年,是我与这处空间和这张小床分离最久的一次。
2021年3月,我因工作调整不再是放映员了,但三楼的这处空间依然是我的念想。床还在那里,我的梦还没有结束,我心里的牵挂一直存在。
单位有我一张床,我就有了依靠和念想,我就会踏实地做梦、过日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