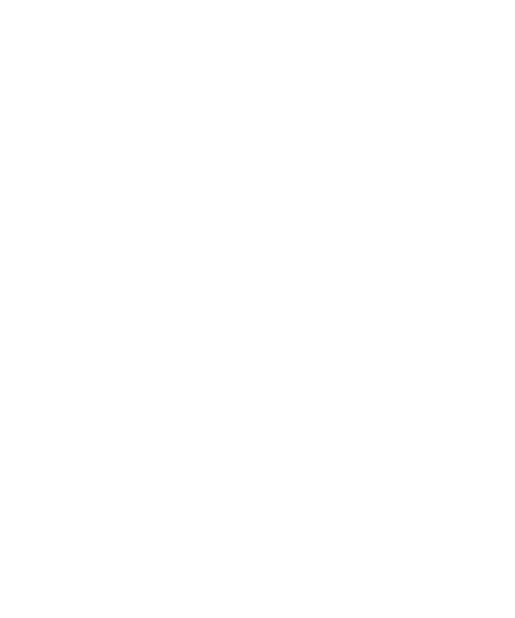□吉 尔
一
我想,那个擀毡子的人一定是走在时间后面的人,一定是默默地守着古老的手艺,把时间卷成一张又一张羊毛毡的人。
加拉力·阿布拉擀了50余年的毡子,库车许多人家的羊毛毡都是他擀的。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都有过一张童年的羊毛毡,我们从那里长大,走到青年、中年,一直往前走下去,有一天忽然发现,那些过去的时间还站在原来的地方看着我们。
这个秋天,我像过去的擀毡人一样走村串乡,他们寻的是生计,我寻的是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古老手艺。
羊毛毡作为人类历史记载中最古老的非编织性织品,距今至少八千多年的历史,最早在游牧人的生活中应运而生。羊毛隔热、耐潮、御寒的特性,使逐水而居、大地为毯的牧民,在游牧随迁生活中始终拥有一所流动的家园。这种归属感曾伴随一代代牧民走出大山,也曾使羊毛毡走向大江南北,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。
我的父亲那一代,是羊毛毡最鼎盛的时期,小时候每到春夏之交,村里家家户户拿出沾染了一年气息的羊毛毡,在铁丝绳上、墙头上、柴火垛上晾晒,用铁锨把、红柳条抽去堆积在毡缝中细密的尘土,高高腾起的烟尘带着浮土的气息,像是把睡了一年的时光也唤醒了。
二
羊毛毡的兴起和发展与各地畜牧业息息相关。畜牧业在新疆社会生产与人民日常生活中占重要地位,畜牧产品曾是人们衣、食、住、行的物质资源。从库车境内岩画推测,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已从事畜牧业生产。魏晋时期龟兹“人以田种畜牧为业”,吕光赞龟兹马为“天骥龙鳞”。据《库车州乡土志》记载,清光绪年间,库车北山和草湖为游牧地,畜皮、毛输往俄罗斯、英吉利。
《库车县志》记载,民国30年(1941年)有毡匠31户,1949年有毡匠92户102人,1954年增至188户332人。1956年成立毡子合作社,20世纪80年代与民族家具厂合并,1990年有制毡企业1家职工22人,产毡2212张、毡靴9双。
在时代的变迁中,羊毛毡逐渐被各类毛纺织加工业所代替。手工羊毛毡制作由盛而衰,这种原始古老的手工艺随着老一辈擀毡人慢慢老去,日常生活中使用羊毛毡的人越来越少,正走向越来越模糊的记忆。
三
在库车市齐满镇甬库团结村,加拉力·阿布拉和黑尼木·加拉力夫妇偶尔会为熟人擀一张羊毛毡。一架陈旧的弹弓是父亲留下的,拨子敲在弦上的声音悠扬遥远。加拉力·阿布拉告诉我们,擀毡子是力气活,一张纯手工擀制的好毡子用五六十年也不会散架。
“我们都是在羊毛毡上出生的,断了脐带先扔在羊毛毡上,来到世界上第一个接触的物品就是羊毛毡。”加拉力·阿布拉回忆起久远的过去,那些留着哈喇子、脸上粘着饭粒在毡子上睡着的趣事。
擀毡人对羊毛毡的情感就像一种命运的相连,仿佛每张毡子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。
加拉力·阿布拉7岁开始上小学,作为匠人的父亲阿布拉·买尔苏认为有什么都不如有一门手艺,他常常带着加拉力·阿布拉四处擀毡子。除了在本县,还去沙雅县和新和县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擀毡子是非常热门的手艺,擀一张2.5×1.5平方米的毡子,工钱是4元,在当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加拉力·阿布拉跟着父亲一边学习擀毡子手艺,一边断断续续上学,到了18岁才上到四年级。说起学习擀毡子,加拉力·阿布拉说,这个活看起来简单,学的时候吃尽了苦头。
由于岁数小,没力气,扛着弹弓用拨子拨弦时动作不协调,不是弦弹起来打破了脸和嘴,就是敲在脚上。因为长期蹲在地上将右脚内旋,加拉力·阿布拉的脚是变形的,走起路来有些跛。
别看简简单单的弹羊毛,弹出一手好羊毛至少得学习四个月。下拨子的时候脸要扭向一边,靠感觉拨弓弦,这样弓弦不会反弹到脸上,即使断了也不会抽到面部。
就连摊羊毛也没有那么简单,用7齿叉一边抖一边摊,摊不均匀就会擀出厚薄不一、带洞的毡子,洒水不均会使羊毛结合不紧密。
加拉力·阿布拉说,毡子擀不好要给主人家赔羊毛钱,父亲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,这样的名誉损害会要了老匠人的命。
父亲告诉他:“一张好毡子应该擀得光滑油亮,看不到一根扎起的羊毛,摸起来手感如丝绸。四边为直线,四角为直角,躺在上面出汗也不粘皮肤。那种加油、用胶或加面粉使羊毛粘合的行当,一个传统的擀毡人是绝对不会做的。”
当初,加拉力·阿布拉用胳膊卷压席子,前臂背侧的皮肤全磨破了,他对父亲说:“胳膊太疼了,想休息一天。”父亲却说:“把胳膊在脖子上蹭一蹭就好了,一个擀毡人不能因为受了点皮外伤就不干了。”
匠人匠心,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韧性。
四
加拉力·阿布拉说,这辈子他最感激的人是父亲,教会了他手艺和身为手艺人要守住的东西。
阿布拉·买尔苏当时是库车有名的擀毡师傅。有一次,加拉力·阿布拉在玉奇吾斯塘乡擀毡子,当地一户人家说起家里有一张阿布拉·买尔苏在1952年擀的羊毛毡。看着这张保存了22年完好如初的花毡,父亲的告诫仿佛又一次在耳边响起:“我们只擀最好的毡子。”
阿布拉·买尔苏擀的是质量和信誉。他年轻时,在乌恰镇一户大户人家织布。有一年,主人家请当时库车最有名的擀毡师傅那尤甫到家中擀200张毡子。那尤甫不仅是擀毡人,也是有名的民间艺人,他的徒弟个个能歌善舞。那尤甫带着20个徒弟白天热火朝天地劳动,晚上载歌载舞,常常参加婚礼、节日等各种演出。阿布拉·买尔苏被这一支快乐的团队吸引,拜了那尤甫为师。从此,阿布拉·买尔苏跟着那尤甫走村串乡,一边学习擀毡,一边学习乐器,很快就掌握了都塔尔演奏技巧,能独立创作歌曲。在擀毡和艺术上的进步,使他成了那尤甫最器重的徒弟。
五
阿布拉·买尔苏45岁时,生了一场病,醒来后忘记了弹唱,但记得擀毡手艺。那一年,加拉力·阿布拉17岁,刚刚出师,他接下父亲的弹弓,带着弟弟开始了擀毡生涯。
加拉力·阿布拉1955年出生,目前是库车毡子手工制作传承人,这个项目于2010年5月入选为第二批地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目前,加拉力·阿布拉能制作出40种花色不同的羊毛毡。
库车羊毛毡有四种,黑毡、白毡、彩毡、花毡。羊毛毡摆放位置有讲究,比如带有树木花卉、几何图形的花毡一般铺在正位最尊贵的地方,也可以当做壁毯使用;黑边红心的彩毡可当“餐桌”铺在中间位置;黑毡一般铺在床边最低席位。过去,从主人家的羊毛毡就能看出家境好坏。
原材料上,羊毛有黑色、白色、灰色、土黄色。按照羊毛质量分三个等级,一级:羊背上的羊毛;二级:腹部和四肢外侧羊毛;三级:羊尾巴周围和四肢内侧羊毛。
每年3月至9月为擀毡子最好的时间,7月为黄金月。加拉力·阿布拉说,气温低的时候羊毛不好结合,擀出的毡子“夹生”。如果冬天客户需要毡子,要把第一遍擀好的毡子在火墙旁烤干,再擀一遍。
一个匠人用传统手工制作一张黑色或白色羊毛毡子需要1天,彩毡需要2天,花毡需要3天。在工序上,以黑毡为例,有分、敲、弹、摊、撒、卷、卷压、撑、拽角、晒10道工序。分,是把羊毛摊开,把羊毛里的脏物和羊粪取净,将羊毛按照绒长和品质分类;敲,是用红柳条抽打羊毛,去除粘在羊毛上的杂物,使羊毛初步蓬松;弹,用弹弓将羊毛弹得蓬松柔软;摊,用5—7齿叉将弹好的羊毛摊在席子上,一般厚度为30厘米;洒,一手拿开水壶,一手拿高粱扫把,将开水倾倒在扫把上抖出水滴均匀地洒在羊毛上,这个步骤水和羊毛的比例与气温有关,靠一个匠人的感觉和经验;卷,用席子从一边开始向里卷,用绳子紧捆席卷,一边用脚蹬一边收绳子,使毡子初步成型,这个过程需要半个小时;卷压,把初成型的羊毛毡移到另一张席子上,一边洒开水,一边卷,为了用力均匀,这道工序基本是前臂背侧用力卷压,需要连续卷压一个半小时,直到匠人用手摸毡子时摸到条绒的感觉,说明毡子已经擀“熟”了;撑,两人抓住毡子两边用力撑扯平整;拽角,将四个角拽成90度直角;晒,把毡子搭起来晾晒一天左右。
这样一张纯手工的羊毛毡就制作成了。
六
加拉力·阿布拉为我们弹奏都塔尔,他的弹奏声引来一起演奏木卡姆的村民。加拉力·阿布拉和妻子黑尼木·加拉力同为库车民间木卡姆艺人,妻子有个好嗓子。
加拉力·阿布拉回忆,他从十二岁开始学习乐器,他的第一件乐器是自己制作的,用牛皮筋绑在玉米秆上。哥哥见他对音乐感兴趣,教给他一些音乐知识,后来他自己学会了都塔尔、萨塔尔等乐器。
如今,需要羊毛毡的人不多了,他们除务农外,经常热心地参加库车民间艺人演出。
此时,那张擀好的毡子晾在围墙上,闪烁着柔软的光,像一种静静地讲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