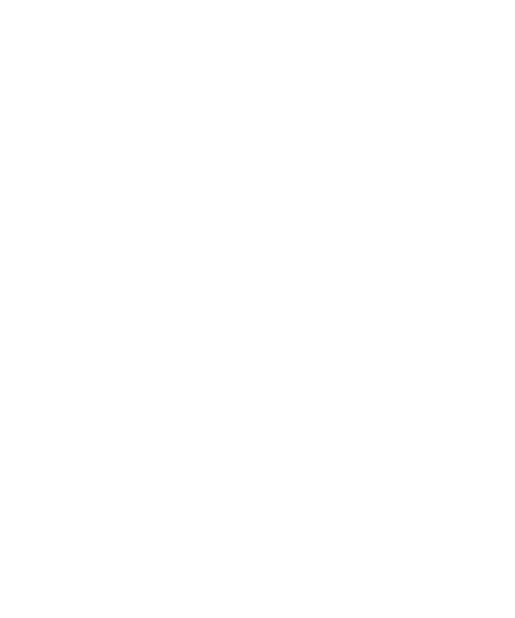本期推荐作者
田万里
1963年4月出生,河南鹤壁人,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,其中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散文诗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文学评论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诗刊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十月》等数十家报刊,多次获奖并入选多本作品集。散文《华山印象》《等你归来》《你走不出这片枫林》《秀发上的女人》于2012年10月分别入选新版《中国散文大系》旅游卷、抒情卷、军旅卷、女性卷,并分别荣获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。
开栏语
阿克苏的美,美在“皮”。蔚蓝的天,洁白的云,冬季的冰雪,春季的碧绿,夏季的缤纷,秋季的硕果,一年四季分明,景美物美食香……
阿克苏的美,美在“骨”。多浪河、湿地、峡谷、草原、沙漠尽展魅力,文化遗址、石窟、博物馆、纪念馆余韵悠长,龟兹文化、多浪文化底蕴深厚……
“阿克苏,一座文化富矿。”近年来,来过阿克苏采风交流的文化名家频频这样称赞。他们走过城市街道,走进乡间地头,漫步河畔湿地,行走草原大漠,流连景区景点……留下一幅幅书法画作,写就一篇篇美文佳作,为大美阿克苏“代言”。
即日起,本报开设“名家看阿克苏”栏目,陆续推出一批名家作品,以飨读者。
大雨已经持续了好几天,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里鸟儿依然在飞翔。车子走过的每一个地方,从窗口扑入眼帘的,尽是属丹霞地貌,山体红红的,就像《西游记》里的火焰山一样,层层叠叠,跌宕起伏,绵延纵深两千多公里。亿万年过去,这凝固的火焰依然燃烧着,始终没有熄灭过。
这些山体在雨中,火焰似乎更加旺盛。各种各样的鸟儿,在峡谷里飞来飞去,数不清的声音融合在一起,尽管鸟儿的身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,但我已经分辨不出它们叫什么了。
这是六月,山坡山的冰雪有些已经融化,有些还在坚持着,不想融化。寒冷浸透了风儿,风儿不断地吹在身上,多么凉爽。零零散散的羊群,在对面的山坡上时隐时现,但只要牧羊人吹一声口哨,羊儿马上就能聚集到一起。
俯瞰谷底,伴随着河水奔腾的声音,浓浓的白色雾气从每一个空间散发出来,袅袅上升。山坡上,峡谷里,那些漫山遍野的石头,像大地支离破碎的语言和沉默。它们厚厚的几层,堆积在寒冷和空旷里。
阳光下,托木尔峰雪山看似很近,其实很遥远,隐隐约约又多了几分妩媚。寒冷就像它的话语娓娓道来,清越之声,使我的灵魂,顿悟到大地的悸动。于是,生命里几乎充满了这些绝美的景色。
当天山突破大地的束缚之时,鸟儿两三声清脆的鸣叫,就像小小的水滴,清越至极。我穿过这样静美的空气,呼吸缓慢且舒畅。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想法油然而生,多年沉积的感觉,从此又流畅起来。重新复苏的渴望,就像鸟儿静静的,或沉默,或啼鸣,继续着从前的脚步和寻找。尽管一些往事已经模糊不清,但细细回想起来,断断续续的,如今却已是朦胧而明快的声音。犹如独库公路盘山而过,久违的那些曲线,在投向远方的目光里,深深地嵌入这些苍凉的空间。
独库公路所穿过的峡谷两岸,一路上都是绝美的景致。乍一看,这些景致都差不多,其实每一处都有自己的亮点和特色。这就是天山有别于其他山脉的地方,看似一样的世界,一旦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有所不同,各有千秋。包括每一朵花,每一块石头。这里是万物重生的世界,是万物尽情绽放的世界,似乎所有的生命,一旦来到这里,就会得到永生。
鸟儿们也一样,尽管它们可以飞翔到更远的地方,但它们在这里的感受却与众不同。就像它们的鸣叫声,在这里是强大的。又似草叶上滚动的露珠,其晶莹的内涵与生命,就是大地庄严的宣言和宣告。
这里的世界与外界可不一样,尽管外界的严寒已经过去,夏天热闹非凡,但到了峡谷,汗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收缩成寒冷的因子,俨然一派冬天的面孔。山坡上,峡谷里不时传来鸟鸣声,就像看不见的冰块,迎面而来,让人不寒而栗。
鸟鸣声不时地在云雾里上下翻滚着。它们从哪儿飞来?又要往哪儿飞去?我不清楚它们的飞行方向。那么远的飞行,不知疲惫的劳累之后,有的只是在这里稍作停留,便又开始飞行。鸟儿们活泼的身影,像草儿在风中摇曳,像泉水叮叮咚咚的声音,悦耳动听。从这些迹象上来看,天山上的冰雪融化之后,点点滴滴,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在一起,一路上声势浩大,奔涌而去。
它们的奔腾从山上冲下来的那一瞬间,似乎就是天山积淀已久的语言,倾诉得惊天动地,诉说得从容不迫。所有的这些,都是冲破大地抑制它们的行为所致。窒息它们,扼制它们,天山在大地的劝说下,深埋着从春天到夏季的一片冲动。它们的等待迫切在泥土之下,久久不肯散去。
冰雪融化,可能只是未来的某个时间。然后,这些景色,就会降伏在夏季的绽放里。顷刻间,或许一株草、一片叶,或许一朵花,或许这里的一切,都会闪现出坚强、坚定的色彩。一朵又一朵鲜艳的冲击,凸显出泥土之下的巨大潜力。
相信每一天,天山的寒冷都是持续不断的。凝固的浪潮起起伏伏,缓缓奔腾着昨天与今天。冰雪下的一朵花儿,突然闪现在我的眼里,它不断地摇曳着馨香。于是,我终于明白了,它是在告诉我,它出生在这里,它已经习惯了。天山脚下的寒冷,就是它习以为常的生活。
鸟鸣声不断从空中传来。也有一些,像雪花一样飘落在地,似乎粘在了我身上。空空荡荡的峡谷里,凌乱不堪的寂静充斥着各个角落。眼前是天山不同的景致,但都在冰雪之下覆盖着,偶尔飘来花香,深深地呼吸一下,就会消失。山坡上的草丛里,有几只鸟儿在觅食,它们清脆的叫声转眼就变幻成了露珠。阳光下,这些露珠晶莹地闪烁着。
这时,一只鸟儿抬起头,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它似乎在端详着我,人与大自然的和谐,就在那一瞬间,重新塑造出了一个新的生命。昔日里,那些破碎不堪的记忆,此时已融入峡谷。
疲倦似乎不见踪影,温暖已归隐山外,耳里充满了色彩。生命在这里仿佛又得到重新修整,就像明快的鸟鸣声。天山上的冰雪,一路从后面追赶着我,但我总感觉,那是鸟鸣的追逐,轻柔而欢快。
站在路边,从山上俯瞰山下,只见满山遍野都是景致,在浓雾之下时隐时现。空荡荡的峡谷里,寒气袭人,单薄的衣服已耐不住寒冷,我只好披上一件外套。
峡谷里的寒冷分子,一个个都张开怀抱,似乎想吞噬我。我却在它们寒冷的色彩和馨香里,尽情地享受着。眼前除了这些美好的景致,我显然已经忘记了其他存在。似乎夏天还很遥远,就像远去的记忆,一切都模模糊糊,好像什么都不存在。
阳光下,天山上的冰雪五颜六色,就像冰川的光芒摇曳在远方,照耀进我的心里。
天山的景致,一路上攫住了我的脚步。盘山而上的独库公路似乎越来越高。已经步入山巅的我,犹如行走在云层之上,呼吸渐渐急促起来。云雾之中,似乎什么也看不到,但鸟鸣声却指引着我,向着鲜花走去,向着天山的源泉深入。这一切看似不经意间的举止,其实都是大自然的引领。
远方的马群慢腾腾地在山坡上啃食草儿。这些马的品种不同,它们身上各种各样的色彩都不一样。有的周身上下都是银色的斑点,有的呈枣红色,色彩炽烈,就像一团红红的火,不知劳累地在草地上奔腾。一会儿它又停下来,仰起脖子,朝着天山大叫。马的嘶鸣声长时间奔跑在峡谷里,甚至要跃上天山之巅,腾飞的身影,瞬间划破了云层。
羊群则在草地上叫声一片。寂静的峡谷自从有了这些声音存在,似乎变得热闹起来。鸟儿们欢快地觅食着宁静,三两声清脆,更添几分神秘的色彩。在天山脚下的山坡上和峡谷里,时时都能听到鸟儿们的鸣叫声。鸟鸣声声,是在欢迎我的到来吗?于是,我的心情愉悦起来,在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,在静静的感觉里,认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在天山脚下,大龙池和小龙池从来没有停止过它们的歌唱。奔腾不止的水流,像鸟儿一样展开了翅膀。我全身心地聆听着它的脚步,凝视着它的身影,仿佛我也是它们其中的一滴。尽管我不知道它的前世今生,但它现在却是人类的向往。一年四季,从来没有见过它的脚步停歇,但它没有怨言。它永远追随着自然的生态,奔腾向前。天山上的冰雪融化之后,不是这两个龙池就能够拥有的。能够挽留住它们的,是一路上的花草植物,是大自然的生态环境。
在这里,一切都是崭新的,包括生命本身的脱胎换骨。鸟儿们歌唱的内容是天山脚下的独库公路,曲曲弯弯,像天山的呼吸,那么炽烈。
其实,天山脚下的歌声,就是这条景色异常壮美的独库公路。行驶途中,听得见它的絮语,就像树叶相互摩擦的声音;看得见它的娇容,就在鲜花盛开的地方。变化就在不变之中。从山下一直行驶到天山之巅,我的大脑里出现了许多生命的变迁,从古至今,时时都会有新的轮回。
春夏秋冬里的景色也是一样,生生死死,交替不断,都是大自然控制下的变化和抗争。可令人困惑的是,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,就像在黑板上随便划出的一道弧线,偏偏有人固守着非生存状态,就是放不下。这始终是一种混沌的状态,而非与大自然共存亡的理性选择。
鸟儿们活泼的身影,依然闪现在峡谷里。空中清脆的鸣叫声不时传来,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天山脚下的空旷和寂静。我似乎沉醉于此。大自然往往就是这样,反反复复,在季节的交替之中,就像人类的生活或生存方式,在无声无息之中发生着改变。比如我眼前所看到的这棵植物吧,鲜花在绽开的同时,它的青春也得到了强有力的释放。在它的视野里,世界就像它的花季一样,让它充满了渴求的欲望。尽管这个世界,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惑,但它的翅膀,高高地举起了天山的壮阔和巍峨。
在天山脚下,似乎我的生命具有了一定的高度,或者说已经进入生命的另一种开始。站在天山脚下,生命的泉源里,激情依然在扩散,感觉依然在涌动。在我身后,可能还有一些未知的脚步,在探索着这里的一切神奇。岂不知,人类的生命,只有融入了这样的环境里,才会有所冲动,有所迸发。那些触动我灵魂深处的,已经驾驭着我,在这里吹来吹去。
看来我在它们眼里,似乎就是恍惚不定的风儿,清新之中,可能还有些特别。从托木尔峰之巅,到天山脚下;从缤纷多彩的山坡上,到蓝天白云奔腾的水流里;从花朵的馨香,到草叶的露珠里;从草原鹰的翅膀,到动物的敏锐感知里;从鸟鸣的清脆,到岩石下的寂静里……就像天山自古以来的沉默,理性地选择了迁徙的鸟儿,选择了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