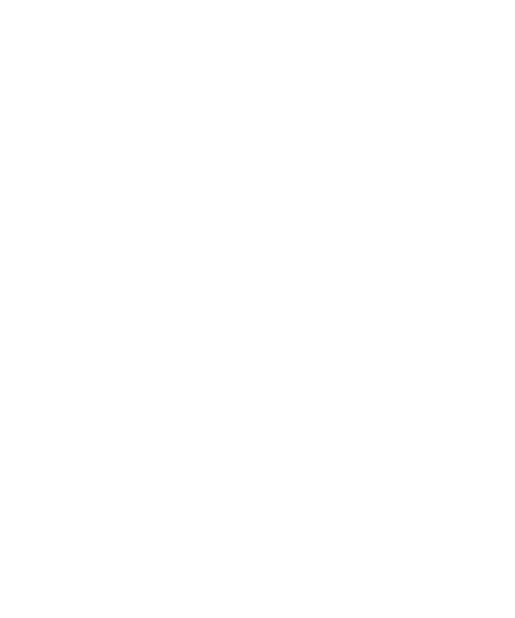仲夏的阳光,将大地撩拨得激情高涨,河边的芦苇像拔节的麦子一窜一寸,叶似韭菜的马莲草直指苍穹,如端午的阳光一样挺拔。“五月五,是端阳。门插艾,香满堂。吃粽子,洒白糖。龙舟下水喜洋洋。”那一首流传千年的儿歌,和着季节的节拍,把端午的粽香送到了我们的面前,让人馋涎欲滴。
粽子,又称角黍、筒粽,属籺的一种,是将柊叶、箬叶、菰芦叶或芦苇叶包裹稻米(或黍)而成的尖角食物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:“芦叶裹米也。”史书上记载最早的粽子为“包烹”,是用树叶包裹以火煨烤的食物,这便是粽子的雏形。从春秋茭白叶包黍米的“角黍”,到汉末草木灰水泡米的四角“碱水粽”,再到魏晋时周处《风土记》的“仲夏端五,烹鹜角黍”,粽子紧随端午,渐入民心。南朝梁人宋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载:“夏至节日食粽,周处谓之角黍。人并以新竹为筒,楝叶插五彩系臂,谓为长命缕。”从吃到戴,端午的内容日益丰富。不管是南来的人,还是北往的客,都不忘在端午节吃粽子,这不仅是一个传统习俗,更是一个民族难以割舍的情愫。
对于端午吃粽子的缘由,最正统的说法是为纪念战国时楚国诗人、政治家屈原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,为追求真理而坚强不屈的精神品行和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操,不仅让屈原成为国士,更是让端午粽变成了高大上。《齐谐》记曰:“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,汨罗之遗风也。”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,被世人永远铭记。一个节日,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,而内涵充盈。端午,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,让人吃粽铭忠,心怀家国。
“角黍包金,香蒲切玉。”粽子虽小,但历朝各代都有自己的新意。从晋代的“益智粽”、南北朝的“杂粽”,到形如锥、菱的“大唐粽子”,宋朝的“蜜饯粽”,再到元、明时的箬叶粽子,以及后来的芦苇叶粽子等,包的主角一直不变,包的佐料总是花样百出。从枣、豆沙到猪肉、松子仁、胡桃,再到火腿、蛋黄等,不断丰富。南北饮食的差异,让端午粽也分成了南北两派。北方以蜜枣、豆沙蘸用白糖、蜂蜜甜性为主,南方以大肉、火腿荤腥为好。不仅在口味上有区别,就连它们包粽子的形状、使用的材质也有很大区别,有竹叶包、马莲草绑的四角形,有槲叶包、线绳子绑的椭圆形,还有一些地方则用槲叶或荷叶一裹了事等。各有各的嗜好,各有各的讲究,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故乡那种芦苇叶包、马莲草绑的四面体粽子。
记得小时候,每年端午临近时,父亲都要张罗着包一锅粽子,以慰家人、以飨亲友。煮熟的粽子如拳头般大小,轻拉活扣,宽衣解带,散发着淡淡清香晶莹透亮的米粒,还有隐匿其中的暗红色枣儿,便脱颖而出。在翡翠绿叶的衬托下,更是光彩照人,轻咬,细腻、糯滑、柔软、清香。若放点白糖,加些蜂蜜,那更是无比香甜。不同的人会将粽子吃出不同的味道。“粽包分两髻,艾束著危冠。旧俗方储药,赢躯亦点丹。”陆游将粽子吃成了济世良药,那是怎样的一个舒心和养胃。“裹就连筒米宿春,九子彩缕扎重重,青菰褪尽云肤白,笑说厨娘藕复松。”卸去层层包装的粽子,在清代诗人吴曼云的笔下,如少女般肤白肌嫩,让人在垂涎欲滴中感叹厨娘的手巧。而袁枚在吃了扬州洪府的粽子后说,“滑腻温柔,肉与米化”,这种仅煨热就需一天一夜的豪华粽子,相信没有几个人能消受得起。
“粽子香,香厨房。艾叶香,香满堂。桃枝插在大门上,出门一望麦儿黄。”端午的歌谣脆生清亮,端午的粽子清香诱人。在走南闯北的生活中,我吃过箬竹叶包的肉粽、槲叶子包的“麻鞋底”粽子,还有艾香粽、薄荷香粽、菖蒲叶粽子等,但心中最合意的还是父亲包的芦苇叶粽子,只可惜今生再也吃不到了,只能把这一种隐藏在心底的味道,和着端午一起咀嚼成鲜活的记忆,一种告慰灵魂的寄托。